

时间:2018-12-20 分类:文学
实践中, 公共档案馆会涉及着作权问题, 对此必须加以研究。公共档案馆中大部分馆藏档案都不会涉及版权问题, 但要注意特殊档案、科技档案和某些电子档案可能会涉及版权问题;在收集档案时, 应当根据档案的来源确定所有权和着作权的归属;对有版权的档案进行编研不要侵犯其版权, 对形成的编研作品享有版权;举办档案展览时要注意美术作品和摄影作品的着作权, 以及国内外对着作权规定的不同;档案公布权和作品发行权是两项不同的权利, 分别由档案所有人和着作权人享有;要根据档案利用者的利用目的、主体、客体、方式、数量、结果等判断是否构成“合理使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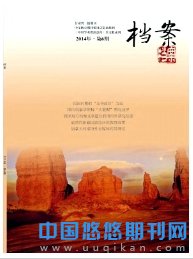
《档案》杂志是由中华人民共和国新闻出版总署、正式批准公开发行的优秀期刊,档案杂志具有正规的双刊号,其中国内统一刊号:CN62-1025/G2,国际刊号:ISSN1004-2733。档案杂志社由甘肃省档案局(馆);甘肃省档案学会主管、主办,本刊为刊。
1、 馆藏档案可能涉及的着作权问题
公共档案馆中的大部分档案都不会涉及版权问题, 包括公务文书类档案、事实汇编类档案 (但为了报道新闻事件而拍摄的照片可被认定为摄影作品[1]) 、通用数表类档案 (如科技档案中附属性或说明性的文书材料和通用材料等) 、公共领域档案 (如文物档案、地方志等, 因超过着作权保护期等原因进入公共领域) 。但是, 需要特别注意以下类别的档案, 可能构成着作权法意义上的作品: (1) 特殊档案, 如人物传记、专利档案、商标档案、名人手稿、信件、知名人士的讲演稿、墨宝等; (2) 科技档案, 来源于科研、生产、基建等科技活动中的科技档案; (3) 某些电子档案,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计算机网络着作权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2006年修正) 第二条第1款规定:“在网络环境下无法归于着作权法第三条列举的作品范围, 但在文学、艺术和科学领域内具有独创性并能以某种有形形式复制的其他智力创作成果, 人民法院应当予以保护。”由此可见, 在网络环境下, 此类电子档案作为版权法保护的客体是明确的。
2、 档案接收征集中的着作权问题
公共档案馆收集的档案, 应当根据其来源确定所有权和着作权的归属。 (1) 国有档案:通过接收的方式把属于国家所有的档案接收进馆, 其所有权和着作权仍属于国家所有, 由公共档案馆代为行使; (2) 购买或受赠档案:公共档案馆可通过购买或接受捐赠的方式获得档案, 如果未购买或受赠其着作权, 那么着作权仍属于原所有者, 但所有权和着作权一并转让给公共档案馆的除外; (3) 寄存档案:寄存在公共档案馆里的档案只是由公共档案馆代为保存, 其所有权和着作权均未转移, 着作权仍归档案所有者。以上三种情况中需要特别注意的是书信类档案。私人书信的所有权归收信人, 然而其着作权却不属于收信人, 而属于写信人, 未经写信人许可擅自发表或使用信件, 可能构成对写信人着作权的侵犯, 也可能会侵犯写信人的隐私权。
3、 档案编研中的着作权问题
首先, 对于有版权的档案进行编研, 要注意不要侵犯其版权。其次, 对馆藏档案进行编研, 编写而成具有独创性的论文、学术专着、方志等, 是享有着作权的, 如上海市档案局 (馆) 工作人员所编的《上海市公共档案馆藏中国近现代名人墨迹》就享有着作权。此外, 公共档案馆组织编纂的期刊、现行文件汇编、档案参考资料等可能构成着作权法意义上的汇编作品。如, 上海市档案局和上海市档案学会主办的《上海档案》杂志上的每一篇文章都是作品, 但是《上海档案》也构成汇编作品, 因为刊物在编辑过程中对文章的选择和编排都付出了创造性的劳动, 符合独创性要求。再如, 上海市档案局 (馆) 工作人员在编写《档案里的金融春秋》时, 精心挑选了档案工作者或历史学者有关近现代史上涉及金融方面重要事件和重要人物的文章, 并进行分类和排序, 由此形成的汇编成果就体现了选择与编排上的独创性, 属于汇编作品。
4、 档案展览中的着作权问题
我国着作权法规定享有展览权的作品只限于美术作品和摄影作品, 档案展览中涉及很多摄影作品, 如果这些作品已经发表, 那么未经着作权人许可布展并不侵犯着作权。需要注意的是, 有一些国家规定的展览权范围比我国规定的要广, 如美国版权法规定的“展示权”不仅适用于美术作品和摄影作品, 还适用于文字作品、音乐作品、舞蹈作品、建筑作品以及电影或其他视频作品中的单个画面, 无论是直接展示还是通过电视、幻灯机等设备放映全部作品或作品的单个画面, 都构成对作品的“展示”, 都是“展示权”能够控制的行为;此外, 我国于1992年加入《保护文学艺术作品伯尔尼公约》 (下简称《公约》) , 该条约规定“自动保护原则”, 即作品一旦创作完成就自动享有着作权, 无须进行登记或发表;该条约还要求各缔约国保护其他缔约国国民创作的作品。所以我国公共档案馆在进行档案展览时, 尤其是赴相关国家举办档案展览时, 会使用一些该国人士拍摄的照片布展, 这时需要注意所在国有关法律规定, 保护照片的着作权, 特别要注意对《公约》缔约国享有着作权的作品进行着作权保护。
5、 档案公布中的着作权问题
档案法实施办法规定的档案公布与着作权法规定的作品发表既有联系又有区别。遗憾的是, 很多学者将公布权和发表权混为一谈, 认为“公布权与发表权一致”[2]“公布权即发表权”[3]。事实上, 着作权法对发表权保护的时间与档案法规定的档案向社会开放的时间不同, 档案开放期限有三种不同情况, 即随时开放、三十年开放和延期开放;而着作权中的发表权是着作权人的一项人身权利, 如果着作权人选择永远不发表其作品, 任何人不得违背其意愿擅自发表。笔者认为, 公共档案馆在公布受着作权保护的档案前, 应征得着作权人同意, 否则存在侵权可能。我国档案法与着作权法关于公布权和发表权存在立法冲突, 需要进一步协调或做出解释。那么对于未公布且未发表的档案, 其公布权和发表权究竟是由公共档案馆行使, 还是由着作权人来行使?再有, 着作权的保护期长于档案的封闭期, 如果公共档案馆公布了满三十年但尚在着作权保护期内的未发表作品, 那么公共档案馆享有的公布权是否侵犯了着作权人享有的发表权?笔者认为, 公布权和发表权是两项不同的权利, 应当分别由档案所有人和着作权人享有, 当两项权利分别由两个不同主体享有时, 一项权利的行使不得侵犯另一项权利, 也就是说, 行使公布权时不得侵犯发表权, 行使发表权时亦不得侵犯公布权。需要进一步明确的是, 作品无论是通过征集、购买还是赠送获得的, 一旦进入公共档案馆成为档案, 那么档案和作品虽然可能处于某个相同载体之中, 即该档案同时也是作品, 但作品和档案是不同的概念, 不能混淆[4]。如果该档案未公布、作品也未发表, 公共档案馆要公布这份档案, 应事先征得版权人同意, 因为档案一旦公布, 也就符合了着作权法意义上的发表行为, 等于代作者发表。但是如果版权人先于公共档案馆公布档案之前行使发表权, 则无须征得公共档案馆同意, 因为作品的发表并不意味着档案的公布。即使作品发表了, 档案也可以是未公布的档案, 这是由作品和档案的不同性质所决定的[4]。
6、 利用服务中的着作权问题
世界各国着作权法中都规定了合理使用原则, 公共档案馆可以享有一系列着作权豁免。如美国《数字千年版权法》 (Digital Millennium Copyright Act, 1998) 第四〇四条规定, 公共档案馆出于诚意, 可以采用数字技术制作数字复制品;俄罗斯民法典第一二七四条规定, 公共档案馆为了补充馆藏可以进行单篇复制;英国《版权、设计和专利法》 (Copyright, Designs and Patents Act, 1988) 第四十二条规定, 公共档案馆可以复制有版权的档案以替代原件;我国着作权法第二十二条对公共档案馆的合理使用作了规定;我国《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第七条对公共档案馆以数字化形式复制本馆收藏的作品做出了特别限定;公共档案馆对档案进行“资料保存”时, 我国着作权法规定了上文所述的“合理使用”。而对档案进行“信息提供”利用时, 《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第七条和第十条从场所、对象和方式三个方面对公共档案馆提供数字化作品作了限定。此外馆际之间的互借行为也涉及着作权问题, 美国着作权法《馆际借阅协议中的复制指南》 (Guidelines on Photocopying under Interlibrary Loan Arrangements) [6]规定了馆际互借制度。英国《版权、设计和专利法则》规定公共档案馆在符合一定条件下可以复制有版权的档案, 但只能复制一份。我国着作权法没有对馆际互借制度作出明确规定。笔者认为公共档案馆馆际互借能否适用“合理使用”原则, 需要从借出档案目的、数量、方式以及对着作权人作品潜在市场影响等方面进行综合考虑。
6.1、 问题的产生
档案利用者在利用受着作权保护的档案时, 公共档案馆如何判断档案利用者是否构成“合理使用”, 是否可以控制档案利用者复制有着作权档案的比例?上海市档案馆规定, 档案利用者复印档案不得超过整件档案的三分之一, 每天复印不能超过50页。如果某件受着作权保护的档案有500页, 档案利用者用10天时间、每天复印50页, 将该档案全部复制下来, 那么公共档案馆能否依据着作权法, 认为其不构成“合理使用”呢?就复制而言, 捷克、巴西、埃及、墨西哥等国的着作权法均规定以一份为合理, 不允许复制多份;也有的国家如冰岛, 其着作权法认为个人复制三份也是合理的。在印刷技术非常发达的今天, 限制复制份数已经没有多大的意义了, 只有限制复制比例才有讨论的必要。2013年, 财政部和国家发改委规定档案利用者可以免费复印档案资料。如果档案资料是享有着作权的作品, 那么免费复制的行为无疑损害了档案着作权人的复制权, 但是根据我国目前法律规定, 又很难认定其“违法”。
6.2、 其他国家的规定
各国法律大都对这种性质的“合理使用”方式作出限制。法国将个人使用限制于私人表演或私人复制;英国着作权法规定出于个人学习或研究目的在公共档案馆复制档案, 复制内容限于杂志中的一篇文章或出版物的一部分;澳大利亚《着作权法修正案 (数字议程) 》 (Copyright Amendment[Digital Agenda]Act, 2000) 规定公共档案馆可以为满足用户研究与学习需求提供档案复制服务, 并向用户传递已经发表或出版的档案资料复制品, 限定条件是一份期刊中只能复制一篇文章, 除非复制的文章属于同一个主题;美国着作权法第一〇八条第七款规定公共档案馆知道或者有足够的理由知道他人连续地制作或发行同一资料的多件复制品, 无论是在同一场合还是持续一段时间, 无论使用目的是一人还是多人, 或者由一个组织单独使用, 均不得适用“合理使用”。美国在司法判例中对个人“合理使用”也作出了较为严格的限制。如美国地球物理学会诉德士古公司案 (American Geophysical Union v.Texaco, 1995) , 作为被告的德士古公司复印美国地球物理学会出版的期刊, 发放给公司员工。法院认定被告侵犯了该杂志出版者的着作权, 因为“一个科学家为了便于使用而复印他人的科学论文存放于个人资料库中是一种存档行为, 目的是为了节省时间免于到图书馆保存的期刊中去检索文章, 这不是为了研究, 不是合理使用”[7]。有西方学者甚至认为应当取消自由复制的特许[8]。
6.3、 认定档案利用者“合理使用”的标准
档案利用者利用公共档案馆馆藏档案, 如要构成“合理使用”, 应结合以下几点进行限定: (1) 目的限定:使用版权档案仅限于学习、研究或欣赏, 不能用于营业目的。 (2) 主体限定:限于满足个人实现上述目的, 这里的“个人”应扩充解释为“家庭”。但是大部分国家都承认公司科研人员为进行研究而使用他人作品的行为只具有间接商业目的, 仍可能构成“合理使用”。 (3) 客体限定:限于已经发表过的作品。档案法第二十条规定档案利用者在符合条件的情况下, 可以利用未开放档案。因此如果未开放档案属于未发表作品, 则不在“合理使用”之列。 (4) 方式限定:合理使用的方式必须合法。要充分保障作者的署名权、作品完整权等及有关出版者的相关权益。 (5) 数量限定:“合理使用”的“量”必须受到严格限定, 只能是“少量”或“适当”。 (6) 结果限定:是否是“合理使用”需接受“三步检验法”的检验 (“三步检验法”是着作权权国际公约规定的判断某一着作权使用行为是否构成合理使用的一般原则[9]) 。“合理使用”不能对作品的潜在市场造成严重影响。
笔者认为, 对于享有着作权的档案资料, 公共档案馆要把复制的数量控制在作品整体量的10%之内;但是如果复制实质性内容或核心部分, 可以认定其不构成“合理使用”。由于公共档案馆所藏档案大部分都不能从其他途经获取, 档案利用者为获取该信息, 只能复制档案, 作为文化事业单位的公共档案馆很难用着作权法阻止档案利用者复制档案行为。也就是说, 从着作权法意义上讲着作权人对于不构成“合理使用”的人, 可以向其出售作品, 但不能阻止其获取信息的权利。当然, 作为着作权人的公共档案馆可以规定档案利用者复制受着作权保护的档案的比例。《各级国家公共档案馆开放档案办法》第十条规定, 由公共档案馆决定复制档案的内容和数量。但是执行这一规定不得违反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的相关规定, 不得侵害公民的知情权。公民利用档案的权利是与宪法赋予公民的生存发展权、受教育权、言论自由权等基本人权密切相关的, 也得到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等法律法规的支持和保护。我国着作权法及其相关条例对公共档案馆使用着作权的程序和步骤以及管理并没有详细规定, 而澳大利亚着作权法则规定用户需要事先填写申请并承诺保护着作权, 公共档案馆也要以一定方式提醒用户尊重与保护着作权;公共档案馆对复制档案资料的具体情况要认真记录并加以保存;公共档案馆可以向用户收取复制费用, 但只能用来弥补相关的成本, 而不允许有额外利润。我国公共档案馆可以借鉴澳大利亚的做法。
需要指出的是, 信息自由是我国宪法默示的一项基本权利[10]。二战后政府信息公开已然成为了一种趋势[11], 但是我国着作权法关于公共档案馆合理使用的规定, 仅仅是为了满足陈列或保存的需要, 这不利于公共档案馆的发展, 也不利于公民信息自由权的行使。笔者认为, 在实践中需注意以下几点: (1) 适用比例原则。比例原则作为我国行政法基本原则之一基本得到认可。修订今后着作权法时, 应当贯彻实施比例原则, 有效控制立法裁量权, 促进立法的科学性[12]。具体来说, 就是要使修改后的着作权法, 在保障版权人的利益的同时, 适当扩大公共档案馆“合理使用”的范围。司法实践中, 在处理公共档案馆和版权人的纠纷时, 法院可以根据比例原则判断是否构成版权侵权。 (2) 司法实践中参照指导性案例。中国特色案例指导制度是我国司法改革的举措之一,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案例指导工作的规定》及其实施细则明确规定, 在类似案件中“应当参照”指导性案例[13]。法院在处理公共档案馆与版权人关于合理使用制度的纠纷时, 应当参照相关的指导性案例。由于公共档案馆和公共图书馆在功能、组织模式、信息资源、服务、标准化建设以及着作权保护等方面有诸多相似之处, 如果没有公共档案馆的指导性案例, 可以参照公共图书馆有关的案例。 (3) 档案部门在着作权法修订时要有所作为。我国立法法第三十七条将法律草案公布征求意见提升成为基本的法律条款, 此举有利于弥补“听取意见”的不足和提高立法质量[14]。笔者在中国知网上以“着作权法修改”为关键词搜索近期的文章, 几乎找不到与公共档案馆相关的着作权法修改建议的文章。档案部门在着作权法律草案公布征求意见时应该有所作为, 积极提出合理化建议, 努力扩大公共档案馆“合理使用”的范围。
参考文献:
[1]王迁.论《着作权法》中“时事新闻”的含义[J].中国版权, 2014 (1) :18.
[2]方开玉.论档案的开发利用与着作权的合理使用[J].档案学通讯, 2000 (6) :43.
[3]蔺清芳.档案管理中的着作权问题[J].中国档案, 2000 (4) :14.
[4][5]赵海军.《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实施后学术界对《档案法》的误读以及《<档案法>修订草案》协调努力之浅析[J].档案学研究, 2018 (4) :34-38.
[6]CONTU Final Report[EB/OL].[2018-10-10].http://digital-law-online.info/CONTU/contu24.html.
[7] Association of Research Libraries[EB/OL].[2018-10-09]. http://www.arl.org/focus-areas/court-cases/2455-american-geophysical-union-v-texaco#.U1voeq6S1pM.
[8] (荷兰) 赫尔曼·柯恩·捷奥拉姆.合法的与非法的复制[J].环球法律评论, 1987 (05) :71.
[9]王迁.知识产权法教程 (第五版) [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6:218.
[10]童之伟, 殷啸虎.宪法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3:160.
[11]何勤华.法律文明史·第13卷·现代公法的变革[M].北京:商务印书馆, 2017:431.
[12]章志远.行政法学基本范畴研究——基于经典案例的视角[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8:61.
[13]余洋.司法义务视域下指导性案例的学理分析[J].江西社会科学, 2018 (8) :50-54.
[14]栾绍兴.《立法法》第37条的法解释学分析[J].法律方法, 2018 (1) :327.